.jpg)
我十多岁时,家搬到了西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儿里。第二天我和我哥就逛了西单,这是我第一次住平房,也是我第一次逛西单。那天我哥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的食品商店买了"话梅"和很多小食品,有些是我第一次吃。
院子是两扇红门,有门铃;一进院子原来是一影壁,后来砌成了一堵墙,只留了一边的走道,把传达室跟院子分开了;院里有圆的月亮门、长廊、十几棵大树,还有一看门人。
我哥那时上中学,他的同学、还有胡同里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每天没事时,特别是放假时就爱凑到我家走廊里打牌、聊天、抽烟。开始我只以为是我哥人缘儿好,后来我才知道,我哥除了仗义,还有就是我家地方大,好折腾,而且走廊里全是窗户,好散烟。大杂院儿里的孩子虽说白天家长也上班,但院儿里的房子紧密,一间挨一间的,这要是哥儿几个凑一块儿来一袋,难免让院儿里的老头儿、老太太之类的闲人抓个正着;我家白天没人,又是自家一小院儿,特别是我爹、我娘回家时就得先按门铃,门房肯定要打招呼,趁着这功夫,哥儿几个早就顺着别的门儿跑了。我就是在这种香烟弥漫的环境下,在我哥朋友的劝道下,好奇地吸了第一根儿烟。

院子挺大,犄角旮旯也多,晚上,我们有时就躲在锅炉房、煤棚子、或别的房子里抽烟。那时象来街正在建地铁,路两边码着很多砖垛子,有时还和一帮朋友到象来街砖垛子后面抽烟。没钱买不了整盒时就到胡同里的小卖铺儿买一分一根儿的散烟,当时“工农”、“战斗”牌儿的烟卖两毛钱一盒。那会儿有首歌叫“工农齐武装”,我们要是买“工农”去,怕大人听明白,也怕别人笑话说抽这么次的烟?就说买“齐武装”去。还有一首歌里边儿有句歌词:“让反美旗帜飘扬在亚非拉上空”,我们那儿一孩子老唱成“在亚非拉战斗”。我们老骂他傻逼,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总忘词,反正他就这么唱,唱时还老露这一脸的坏笑。后来我们要是想买“战斗”的就说买“亚非拉”的。有一次让一不明就里的孩子去买“亚非拉”去,这孩子知道我们说的是烟,就假装特明白似的接过钱往小铺儿跑。他花了四分钱买回来五根儿阿尔巴尼亚烟,就细支的、抽起来特别臭的那种。
回来后有人埋怨他也不问清楚了就瞎买,假明白!他特委屈地辩道:你们的意思不就是想买外国烟嘛?
奥~“亚非拉”就是外国烟呀?有人接着唱到“越南人民举铁拳,把美帝打得焦头烂额;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,放射出更加灿烂光辉。”孙子,人家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!
这孩子也唱到:“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。”孙子,知道什么叫节约,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吗?
大家嘻嘻哈哈...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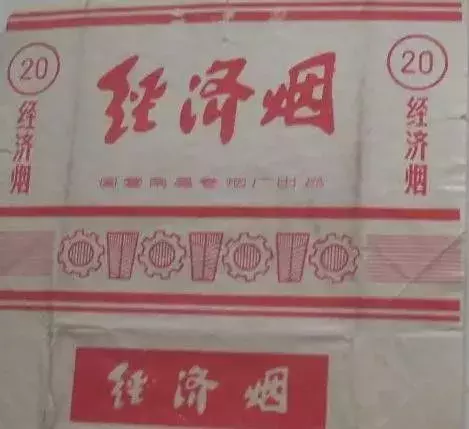
每当我一买散烟时,小铺卖东西的老太太就盯着我问,给谁买烟?是给你爸爸吗?我知道你爸爸是那个当兵的。弄得我浑身不自在,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老太太那善良、严厉的目光。其实那时抽烟只是好奇。
在那住了三年,我家又搬到了一个大院里。我和哥哥都有个毛病,就是总爱跟比我们大的孩子玩儿,他们的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我们都爱跟着瞎掺合,他们也没小看我们,我们在心理上也没觉得比他们小。
那时院里的孩子下班了、放学了都爱凑到一起打牌,打牌就要抽烟。其实那时我并没什么烟瘾,拿抽烟当成一种交往的手段,那时你要是找一群哥们儿帮你平事,要是从书包里拿出一两条"大前门""牡丹"之类的烟,把整条的烟两手一撅,往哥几个面前一扔,那今天的事就不用再嘱咐什么了。再就是抽什么牌子的烟就好像是身份的象征似的,特别是七四年、七五年那会儿刚有黄盒"凤凰"烟时,一抽,满屋子香味儿,牛!那时"凤凰"烟也不是那么好买的,有的孩子就把铁烟盒里放上白色的小颗粒香精,抽起来也散发着一股香味,觉得也挺牛。
院里有一哥们儿当时在友谊宾馆上班,他经常往家里拿"中华""牡丹"之类的散烟,我问他哪来的这么多好烟?他说客房里每天都要往小盘里放十根儿烟,有的客人不抽也不拿走,最后他们就自己留下抽了。我们有事没事的常上他家蹭好烟抽。
那时哥们儿中也有常蹭烟的主儿,不带烟不带火的叫一级蹭烟,带火不带烟的叫二级蹭烟,这样的主儿一般让人看不起。有拉的下脸的哥们儿,在发烟时就成心不发给这样的主儿,有时往往为一颗烟大打出手,结下恩怨。那时小孩儿抽烟,一个是偷家长的,再一个就是把家长给的吃早点儿的钱、理发的钱拿来买烟,我理发的手艺就是那时练就的。

院里还有一哥们儿,在京郊插队,家里管得挺严,烟瘾又大,探家时一犯烟瘾就往我家跑。我就纳了闷了,丫是如何把自己练就成一杆烟枪的?他告诉我,农忙时,你要是耪地耪到地头儿,站在那慢慢地卷上一炮,抽袋烟借机歇会儿,没人管你;你要是戳着锄头愣会儿神儿,想直起腰来缓一闸,队长就得说,干嘛呐?又想大姑娘了?还不快干活儿。冬天,农闲时,大家没事聚一块儿侃大山就更得抽了,“烟暖房,屁暖床”。
因为这哥们儿在生产队里赶大车,我们就按电影《青松岭》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钱广。那一日,见他提着一大口袋进了我家,我想起了《青松岭》里钱广走资本主义道路,往城里贩卖榛子的情节,我说:怎么着,把榛子口袋提这儿来了?
他一笑,顺手把口袋扔到了桌子上,我打开一看,原来是烟丝。他说:三斤,且抽呐。
三斤!您想想那得多大一包啊。"榛子"口袋一直放在我的床下,后来这哥们儿到我家玩儿,每当哥几个玩到夜里弹尽粮绝没烟时就想起了它,总有人忍不住高声喊道:拿榛子口袋来!我跟我哥要是没烟时,也会把"榛子"口袋提拉出来。我这人手笨,不会卷"大炮",就花了一毛一买了一个铜锅儿花竹管的烟袋锅儿。后来就是这"榛子"口袋和烟袋锅儿把我"害"得几乎一闻烟味就想吐。
有一次哥几个玩着玩着又没烟了,我拿出了"榛子"口袋,哥几个一人卷了一大炮,我也捻上一锅儿。捻烟丝时就觉得大拇指有些发粘,当时就以为是烟袋油子或是汗之类的,没在意。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烟里有什么东西往外炸,把“大炮”都炸开了,我的烟袋锅里的烟丝都炸出来了,谁也没在意,后来抽着抽着就觉得嘴里不对味儿,而且屋里也充满了一股烧肉皮的臭味儿。不对路子,我拿过口袋,捏了一撮烟丝,就觉得手里粘糊糊的,细看,原来烟丝放得时间太长了,烟丝里长满了浑身全是小绒毛小白肉虫子,个个活,再看烟丝,就好像一个会动的球。烟里会炸的东西,还有这一屋子臭味儿都是小虫子弄的,真他妈的恶心。从那后一闻到烟味,我眼里、手里、嘴里、鼻子里好像都能感觉到小虫子的存在。
我抽烟上瘾还是当兵后,那时每月每人发给两张烟票,一张票一条烟,两张票,一条好烟一条次烟。好烟是"长江"牌的,三毛四一盒。买!不买就觉得太亏了。烟是当时沟通感情的主要工具,到哪兜里都揣着烟。
那时哥儿几个一聊天,就总有人拿出几盒好烟,不抽完不让走,不抽都不行。我当时很不适应南方的气候,总觉得气压低喘不上气来,再加上烟抽多了就更觉得气管儿发紧。这时总有好心的哥们儿端来一大缸子凉水来,十分关切地对我说:哥们儿,喝点凉水冰冰,一会儿气管儿就舒服了,再接着抽。
其实,抽烟对我是件挺痛苦的事,我总怀疑自己是哮喘,但在那个环境里又戒不了。有个北京兵,个子不高,平时总受人欺负,我对他挺好,只要见谁欺负他,不管是干部、战士,新兵、老兵,我都要管。他对我也挺好,好像离不开我似的,整天跟我膘在一块儿。见我说自己有哮喘,他说他爸也有哮喘病,也戒不了烟,每天抽一种叫曼陀罗花的东西。既能过烟瘾,又能治哮喘。我问哪有这东西?他说哪都有,就是路边上长的跟蓖麻是的那东西。

他还告诉我,把花踩下后晾干就能抽了。可南方的天气太潮,踩的花总也晾不干。后来他给他爸写了封信,他爸给我寄来了一大包。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爸就寄一回,直到我调回北京还没抽完。
我回京后分到一家医院门诊工作,有一次我抽曼陀罗花,有一医生问我抽的是什么?那个年代,在别人看来,我不是一个太守本分的人,好像我做什么事大家都要问个为什么?我说是曼陀罗花。他很吃惊,严肃地告诫我这东西不能随便抽。
我问为什么?
他给我讲了一件事,说有个老师长,是个解放干部,原来在国民党部队时就是师长。解放前抽大烟,解放后不抽了,但总也戒不掉,就抽这个。有一次抽多了,光着屁股,头顶着一尿盆就跑出来了,这东西抽多了容易产生幻觉。从那后我才知道,原来李时珍发明的"麻沸散"就是以这东西为主料。
想想哥们儿还是个童蛋子,要是哪天抽多了,跟老师长似的也弄一裸奔,把青春暴露无遗,那可就瞎了。从那以后就再没敢抽过这劳什子。
我弟那时不抽烟,但很喜欢好看的烟盒,七九年、八零年那会儿北京总举办轻工展之类的活动。展会上总有很多新牌子的烟,我弟总爱买回来,如一块二一盒"颐和园"、"天坛"之类的烟,结果总是我抽烟他留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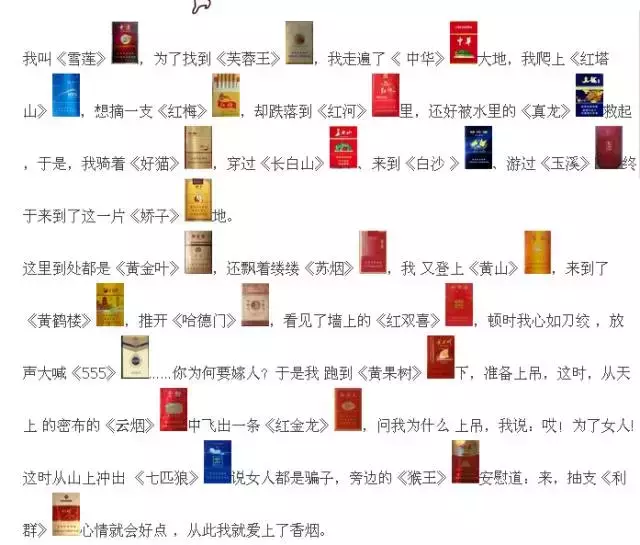
后来到了地方,烟更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当时到哪去办事你要是不给对方上颗烟,要不就是办不了事,要不就是办了,也没好脸。我们单位搞业务的、开票的,别管男的、女的,抽不抽烟,一天下来抽屉里往往能收一堆散烟。记得当时《北京晚报》就有一篇一分钟小说,写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儿出门办业务,虽然自己不会抽烟,但兜里总装着一盒好烟,逮着谁给谁上烟,说的就是当时那种不正之风。

再后来社会"进步"了,上烟也由根儿到盒、由盒到条。到我八十年代末搞业务时,送烟已成了人之常情。我的口味也从国产烟改成了进口烟,我当时最爱抽的是"万宝路",为此没少有人向上级反应我的抽烟问题。有人给我算了一笔账,就是把全月的工资全用来抽烟也不够烟钱。确实如此,那时一个月就挣一百多块钱。后来这事反映到了领导那,领导在会上说,一个业务干部,客户给送点好烟不算什么事。也是,领导比我抽的烟还贵呐,反映我不就跟骂领导一样吗。

让我最难忘的一条烟,是太太送我的十三块一条"金健"牌的烟。八几年,太太单位号召人人做生意,那会儿是“十亿人民九亿倒,还有一亿在思考”的年代。她当时岁数小,从来没做过生意。一次,太太跟同事忙活了一天,每人挣十几块钱,回来时给我买了这条烟。她不懂烟,拿了钱后就进了一家食品店,用当天挣来的十三块钱,买了当时店里最贵的烟。太太当时脸上那种疲惫、自豪的表情我至今难忘。
九十年代初我"下海"做生意,周围的朋友大多抽"三五",我也改成了抽"三五"。九十年代末,我到一家银行办事,行长拿出"中南海"烟招待我,我问怎么抽这烟?他答,和一家烟酒公司合作,烟酒公司送了两厢这种烟,这烟挺好抽,而且还没有假烟。临走时他送了我几条"中南海",觉得口味确实不错,打那后我就开始抽"中南海"。
我觉得抽烟喝酒就是个口味和面子的事,您要是说哪个比哪个危害性更小,哪个比哪个更有营养,只要是正经厂家生产的,差别不大。要是真怕有害咱不抽行不行?要是真想补养,咱喝点儿蜂王浆成不成?

我们院有一哥们儿,每天早晨起床必须先抽两袋烟,紧接着就是一通"咳咔"乱咳嗽,紧接着就是两口粘痰,这才倍感舒服,他说这叫"勾痰逗咳嗽"。我不行,我有个习惯,早晨、上午基本不抽烟,好像肺还没活动开;下午晚上抽得多,要是夜里再有个活动,那就没了谱儿了。
近些年来,夜里也觉得痰多了,这跟抽烟肯定有关系。几次想借着感冒咳嗽把烟给戒了,因为我一到此时抽烟,嘴里总有一股啃了墙皮的味儿,但戒不了多久,等病一好就又开抽。
前几年,香港足球界一朋友,也就是原香港“愉园”队的教练,后来协助香港富豪杨家诚入股英超伯明翰俱乐部,也是该俱乐部的副主席余怀英先生来京谈事,我见他抽的是英国一种细支的女士烟,我觉得挺奇怪。他说他也是因为戒不了烟,就抽这种烟,这样可以少吸进点儿烟去。他劝我说,小京,你也吸这种烟吧。我说,是不是看着有点儿娘们儿气?余先生说,别管什么气,对身体损害小点。后来见当时"国安"队主教练、韩国人李章洙也抽细支烟,我也就改了这种烟了,每天还真能少抽不少烟。
为这事还差点儿没闹出误会来,一次我们一哥们儿得病,我去他家看他。聊天中我抽了几颗烟,过了一会儿他媳妇回来了,看见烟缸里有很多女士烟头儿,就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。我一看他媳妇表情不对,就又掏出了烟抽了一颗,他媳妇怀疑地看着我,以为我俩是在演戏,为他掩盖着什么。这一下午,我是一颗接一颗的抽,直到打消了他媳妇的疑心。够累的,真练肺。后来我跟他说,看来咱们不但需要铁胃,还需要铁肺。

就这样,我抽烟由抽北京烟改成抽云南烟,又由烤烟型改成混合型;而且是抽了戒,戒了抽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人家说“饭后一袋烟,赛过活神仙。”我倒没这感觉,我就是累了、紧张了、还有酒喝多了就想抽烟。
去年小侄子放暑假回家,开车带着我和我弟、还有我们家老太太先去了十里河花鸟市场溜达,后来又去了官园花鸟市场。我在"官园"买了一个烟斗,又买了二两烟丝,我当时想,抽烟是一种习惯,有时烟瘾上来了,抽一两口就行,买个烟斗叼着,想抽时点上抽两口过过瘾就行了。
回家后一抽,真没想到,抽烟斗是个力气活儿,点着后抽不了两口就灭,细看,原来买回的烟丝太潮,想抽,就得玩儿命嘬;好不容易着了,抽到嘴里倍儿辣,全是烟袋油渍,也不敢咽口水,还得使劲嘬干嘴里所有的口水往外吐,嘬的腮帮子直疼;就这样,口水不小心流进了烟管儿里,又被吸到嘴里,循环往复地洗刷着烟管儿,一次次使劲地吐着唾沫。有时不小心,要是咽进去一两口混杂着烟袋油渍的口水,食道里就觉得火辣辣的、揪着的感觉,为什么有些人浑身抽搐就被形容为跟吃了烟袋油渍似的?今儿我算是真有了切身体会了。没几天我就觉得舌头、上牙膛子发涩,还有些疼,原来是嘬的太使劲了,把嘴里皮都嘬坏了。
每次打麻将时为了少抽烟,我都叼着烟斗,还是用后槽牙横叼着,可用两手洗牌时,烟斗就在嘴里晃来晃去,硌得槽牙倍儿疼;后来竖着用几颗牙咬着又觉得不方便。有一次,没烟丝了,我便把纸烟拆开了放进烟斗,没想到,一锅儿竟能放进去四颗烟。操的嘞!每次不但没少抽,还加大了剂量。我说怎么抽完一袋这俩鼻子眼儿感觉这么干,呼呼往外冒热气儿,跟俩小火炉子眼儿似的?一想,受那个罪呐,下决心少抽点不就得了。

没几日,又改成抽细支的女士烟了。前天,小田来京,晚上几个朋友在亚运村聚会,我和太太八点多赶到,席间我拿出烟抽,有的朋友早已习惯,见怪不怪。其中有一久未谋面的朋友甚觉奇怪:我操,冒充当代秋海棠是不是?
我掐着嗓子拉着长声、细细喊了声:相公......
作者:潘小京

